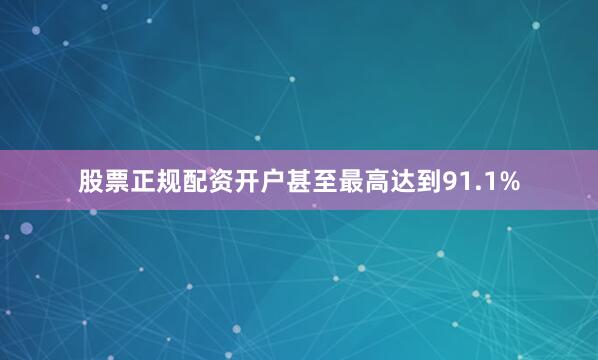作者:朱通华
“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市委写作组和北京两校大批判组,是“四人帮”的两支反动笔杆子,臭名远扬,罪恶滔天。正如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所点名定性的:它们“连篇累牍地炮制反动文章,宣扬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充当‘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
江青曾经声称:“林彪有舰队,我军有炮队!”上海这座城市中的这支写作团队,实则成为了“四人帮”篡党夺权行动中的一支“炮队”。该团队由张春桥与姚文元精心栽培,并始终被他们牢牢掌控。
上海写作组正式于1971年7月宣告成立,然而,其与徐景贤担任支部书记的上海市委写作班,以及以朱永嘉、肖木、王知常为领导核心的《红旗》杂志上海组稿小组,均存在着密不可分的深厚历史联系。鉴于此,当我们回顾上海写作组的兴衰历程,不可避免地会发现徐景贤、朱永嘉、肖木等一众人物是如何历经造反起家、搅动上海局势、最终自食其果这一历史轨迹的。

1969年四月,中共九大的主席团成员中,徐景贤有幸与毛泽东同志进行了一次亲切的交谈。
“徐老三”造反
自1967年起,十年间,有谁不识上海滩的徐老三?他便是徐景贤,出身于奉贤县奉城,曾在解放初期的南洋模范中学接受教育。1951年,他被选调至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服务。1956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他担任了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的职务。
1966年11月,徐景贤正专心致志地为当时的主管领导——市委宣传部长撰写检讨书,与此同时,他正与张春桥、姚文元交往密切。两人已进入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在直接领导下,他一夜之间发动了“造反”行动,试图夺取上海市委的权力。自此,徐景贤的仕途平步青云,直至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其地位仅次于张春桥和姚文元,成为上海排名第三的领导人。因此,人们便称他为“徐老三”。
徐景贤的“造反史”篇章,始于复旦大学红卫兵对朱永嘉、姚文元的揪斗,以及他于深夜时分与姚文元的电话交流。
朱永嘉,昔日复旦历史系的一席教授,兼系党总支委员之职。彼时,他受借调于上海市委写作班,以“罗思鼎”之笔名,著文问世。至1966年11月25日,复旦大学红卫兵将他押回校园,责令其交代在校期间所持的修正主义观点及言论,并要求其交代在上海市委写作班撰写的修正主义文章,同时亦迫令写作班交出文章的底稿。
“文革”的烈焰蔓延至上海市委的写作班,若任其肆虐,恐将波及张春桥、姚文元的领地。写作班负责人徐景贤心急如焚,急忙拨通中央文革小组的电话,向张春桥、姚文元发出紧急求援,声称将积极投身“造反”行列。
张春桥在接到电话的那一刻,语气中流露出一丝满意,轻声回应道:“甚好。”紧接着,他又补充道:“关于具体实施的方法,我们还需进一步进行探讨和研究。”
张春桥与姚文元,连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密谋策划后,于11月29日,姚文元亲自致电徐景贤。
姚文元在通话中声称:“复旦大学那些造反组织,是不是想要挖掘罗思鼎的幕后支持者?幕后之人正是张春桥,还有我姚文元!你们尽管来查!”此外,他还提及:“戚本禹得知此事后同样感到震惊,他打算将大字报送到复旦大学去!”徐景贤当时将
朗读(在左翼阵营中朗声)姚给丁(亦即丁学雷,徐景贤惯用的笔名)电话:
(1)传闻复旦党委执着于贯彻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对罗(思鼎)小组进行整治,并对朱(永嘉)展开批判。姚(文元)、张(春桥)对此感到震惊!关(锋)、戚(本禹)则满腔愤怒……(2)实则关键在于:根本问题必须直截了当,明确指出本单位、本校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朱的问题为何突然受到批评?究其根源,实则指向张春桥。
(一)中央文革小组坚定地支持朱永嘉。坚决制止对朱永嘉的追查,因为其目的直指张春桥,绝不可容忍。
(二)旨在将火焰引向复旦大学党委,使其背负上“秉持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的指责。

1965年9月,徐景贤(居中,后排左侧)有幸作为中国青年文艺工作者代表团的成员访问越南,受到了胡志明的亲切接见。
迅速间,局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反转:朱永嘉得以获救,而罪名则尽数落在了复旦大学党委身上,同时牵连了市委教育卫生部和宣传部,三者均遭到了激烈的批判。
张春桥与姚文元对此并未轻易放弃。12月12日,姚文元再次拨通徐景贤的电话,询问:“市委写作班是继续执笔撰文,还是投身前线工作?”
所谓走上第一线,即意味着要奋起反抗,不仅要挑战复旦大学的党委,更要将反抗行动推向更高层次,直至触及上海市委的核心。
徐景贤沐浴在这片“大气候”之中,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深觉此次反抗的“苗头”愈发旺盛,势头愈发强劲。
12月14日的夜晚,徐景贤主持召开了写作班全员大会,向与会人员传达了张春桥与姚文元的“指示”,并就此如何发动抗议展开深入讨论。会上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主张班内成员各自返回各自的工作单位发动抗议;第二种观点则是直指市委宣传部进行反抗;第三种意见则是将抗议的目标锁定在上海市委。经过整夜的激烈辩论,最终达成了共识:全体成员一致决定发动抗议,目标直指市委。
徐景贤郑重地向大家表明立场:革命的道路上,北京显得格外亲近。我们须紧密跟随春桥、文元同志的脚步,紧随中央文革小组的指引,对上海市委展开批判。春桥、文元同志对我们关怀备至,我们绝不能辜负他们的厚望。
在激昂的号召下,人群中有人挺身而出,高声呼喊:“春桥、文元同志呼唤我们奋起反抗,我们不能再拖延,绝不能继续沦为上海市委的附庸!”
有人提议道:“写作班乃是一座坚固的堡垒,其战壕可延伸至各个部门,比如办公厅、教育卫生部,以此串联各方力量,共同发起反抗。”
有人便提出:“我们必须投入实战,拿出真正的武器弹药,内外夹击”,“必须直接与中央文革小组取得联系”。
自写作班发起反抗行动后,随即与上海市委机关的刊物《支部生活》的造反队伍合并,共同成立了“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该造反组织在随后的“一月夺权”运动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曹荻秋自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其立场必然极端顽固。你们在制定策略时,需更加深思熟虑,以期达到更为显著的成效。”
姚文元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然而,我们绝不能止步于此。我们必须做好更深入的挖掘工作,准备揭露陈丕显、曹荻秋的问题,并一举将上海市委拉下马。”

1967年夏日,周恩来总理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首次莅临上海,与徐景贤等人士进行了会面。
“炮击上海市委”、“焚毁陈丕显”、“挖掘曹荻秋”、“推翻杨西光”、“摧毁常溪萍"。
这些口号,出自徐景贤与北京大学造反派的领军人物——聂元梓,彼时她正因串联造反活动滞留于上海,双方遵照姚文元的指示达成一致。张春桥曾多次对之赞誉有加,称:“这个口号颇具策略!”
我们,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全体成员,以及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徐景贤(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罗思鼎小组负责人),郑重宣布:我们的决心已定,誓要反抗上海市委所坚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抵制市委内部那些妄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少数当权派!我们要彻底地进行反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声明》进一步指出,自批判《海瑞罢官》之作始,他们便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领导下,沐浴于革命青年造反精神的熏陶之中,投身于斗争的洪流。
只有徐景贤、朱永嘉等人,才是真正的造反先锋。
自此次大会召开之后,由徐景贤领导的“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实质上沦为张春桥、姚文元操控上海市“文化大革命”运动及夺取上海市委权力的工具。在张春桥、姚文元成功实施“一月夺权”后,该联络站更演变为他们身边的执行团队。徐景贤也因此跃升至上海政治舞台的核心位置,成为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操控下挥舞利刃的关键人物。

1973年9月16日,徐景贤随同邓颖超,一同前往上海虹口公园,拜访鲁迅先生的墓园。
张春桥托徐景贤
为他“找个伴”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与姚文元自北京返抵上海,以“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作为他们的工作据点。徐景贤因而愈发觉得荣耀加身,身份也随之水涨船高。
直至1967年年末,"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内部分化为两大阵营。其中一派对徐景贤持反对态度,一度令其处境堪忧。在危急关头,张春桥提议徐景贤担任上海市党章起草小组的核心成员之一。此举实为张春桥对徐景贤信任与支持的明确表态,进而稳固了徐景贤的局势,使其转危为安。
自1969年中共九大落幕之后,徐景贤的仕途如同腾云驾雾,一路攀升至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高位。自此,他愈发明悟,张春桥、姚文元正是他得以稳固立场、步步高升的坚实后盾与坚强依托。
张春桥曾对徐景贤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且两次态度尤为激烈。然而,这些批评实则出于让其稳固立场、减少失误、更加顺从的考虑。张春桥与徐景贤之间的联系究竟如何?他对徐景贤的信任又有几分?以下一例具体事件便能揭示真相。
1976年二月末,中央召开了所谓的“批邓打招呼会议”。在2月26日的夜晚,张春桥在约谈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时,向他们提出了寻找两位秘书的要求。徐景贤返回上海后,迅速挑选了两位男性干部,并整理了相关材料,随后在马天水和王秀珍的审阅下,将这些材料寄送给了张春桥。
坦白讲,我所寻求的并非普通秘书,而是一位伴侣。我的境况,想必您也有所了解。近年来,时常琢磨,人生无常,说不定何时便会遭遇不幸,何必纠结于这些琐事?然而,孤独时又常思及此事。您看,是否有可能找到合适的人选呢?
信的末尾写明:
前页内容可供同仁参阅,此页请于阅读完毕后予以销毁,以避免招致不必要的不快。
张春桥,这位性格阴郁、内心深沉的大野心家,竟然将“寻觅伴侣”的重任托付给了徐景贤去处理,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徐景贤的深厚信赖与倚重。关于此事,徐景贤事后曾如此说道:
恰似天意弄人。“四人帮”于1976年10月6日宣告覆灭,而徐景贤恰巧在这一日向张春桥寄出了所谓的“伴”之资料。自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来,徐景贤在受审查期间,此事始终是他心中的一块难解之结。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
批判《中国画》
矛头指向周恩来
在1973年左右,周恩来总理致力于提升对外贸易水平,针对当时盛行的极左思想,他明确提出:只要工艺美术品不含有反动、低俗、丑陋元素,就应组织生产和出口,并强调内外有别的原则。他进一步指出,将此类产品销售给外国,用以换取外汇支持社会主义建设,并无不妥。基于此,周总理亲自关注并处理了宾馆装饰画及外贸出口画的相关事宜。
至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拉开序幕之际,“四人帮”为迎合攻击周恩来、谋取党权的目的,便气势汹汹地对宾馆内的画作以及外贸出口的美术作品发起了猛烈攻击。
江青率先发难,张春桥与姚文元紧随其后,文化部官员于会泳立即拨通徐景贤的电话,进行情况通报。1974年伊始,姚文元在上海向马、徐、王等人传达“指示”之际,突然出示一本《中国画》画册,要求众人传阅。他本人亦指指点点,逐一进行严厉批判,诸如“这画中的山川如同黑山黑水”,“这只公鸡的尾巴似乎翘到了天际”,“这无疑是一本彻头彻尾的克己复礼之作”,语气中充满怒火,杀气逼人。

陈大羽《迎春》画
一旦风吹草动,徐景贤便迅速行动。3月6日,他借助市委办公室文件的名义,公开发表了“市委领导同志对《中国画》的意见”。在其文中,徐景贤如此阐述:
这本《中国画》画册集中揭示了我国外贸领域及美术创作中存在的诸多严峻问题……
总的来说,面对外汇交易,部分同志表现出右倾投降的态度,他们不仅不以这样的作品为耻,反而引以为傲。作品名为《中国画》,那体现伟大社会主义中国人精神的气概究竟去了何方?
3月20日,上海的《文汇报》与《解放日报》不约而同地刊登了徐景贤亲自定稿的长篇评论文章,文章标题为《一本地地道道的复礼、翻案的画册》。
3月28日,徐景贤再次对两报作出批示:“针对《中国画》的版面批评,需持续推出数版。版面设计时可标注全栏标题:‘深度剖析克己复礼,坚决抵制美术领域的复辟逆流’,以与北京即将启动的批判活动相呼应。”
此后,上海两地报纸纷纷连篇累牍地发表相关文章,对事件进行大批特批,每篇文章均由徐景贤亲自审定。此外,徐景贤还策划了“坏画”展览,并主持召开了数千人的批判大会,气氛热烈,场面火爆。
这幅画作生动地展现了一只怒发冲冠的雄鸡。其喙紧闭,鸡冠高昂,颈羽张扬,双爪紧紧抓住地面,眼球翻白,目光怒瞪,尾巴更是高昂至云端。这画面显然并非在欢迎新春,反而是对社会主义春天的强烈抵触,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所涌现的生机勃勃景象的极端反感。
在这只公鸡的身上,映射出了当代社会一小部分“复辟狂”的阴暗心态。他们对于自己的失败耿耿于怀,时刻准备与无产阶级展开一场殊死搏斗。
徐景贤与该批判文章的作者,不仅为这幅画作贴上了令人畏惧的政治标签,更是将“复辟狂”的“反革命”罪名强加于画家之身。

1972年五月,徐景贤率领代表团赴朝鲜进行友好访问,荣幸地得到了金日成主席的亲切接见。
请问,《迎春》这幅作品的创作者是谁?答案是南京艺术学院的陈大羽教授。陈教授不仅在政治立场和艺术造诣上均堪称典范,是一位资深的画家。然而,徐景贤究竟有何理由,未经事先与江苏省相关组织进行任何沟通,便采取偷袭的策略,将指责之词指向邻省一位共产党员教授呢?
徐景贤的险恶用心,显然并不仅限于对陈大羽教授个人的攻击,其背后有着更为深远的图谋。他意图通过打压兄弟省市的文艺创作与创作者,假借“挖幕后”等手段,以稳定上海的局面,同时制造全国范围内的混乱,此乃一桩祸国乱邦的罪恶勾当。
自1971年7月上海写作组正式成立起,至1976年活动终止,它追随“四人帮”的脚步走过了五年多的时光。该组织的影响力渗透至上海各条战线,乃至全国多个地区;其触角之广泛,影响之深,涉及历史、经济、宣传、文艺等各个领域。它不仅创办了各类刊物,撰写文章,还涉足文艺、调查、党史编纂、教材编写、翻译等工作,无所不涉,无所不包。旗下刊物共有8种,包括《学习与批判》杂志、《朝霞》月刊、《朝霞》丛刊、《自然辩证法》杂志、《教学实践》杂志,以及《外国文艺摘译》、《外国哲学经济历史摘译》、《外国自然科学摘译》等。发表文章约800篇,其中《红旗》杂志刊发76篇,《学习与批判》杂志刊发774篇。其影响之广、能量之巨、危害之深,令人瞠目结舌。

杠杆炒股官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