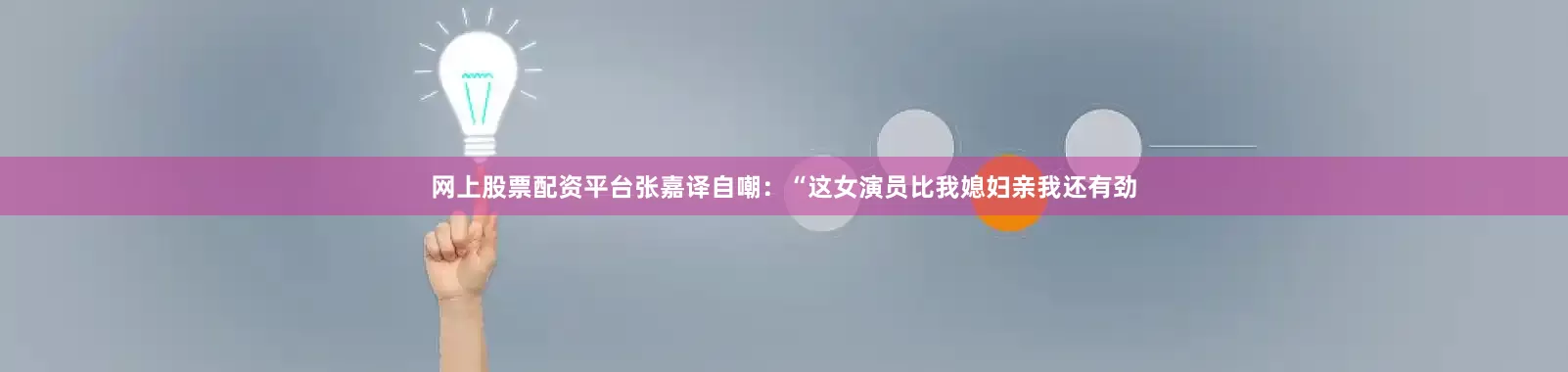在陈玉成阵亡后,其麾下将领陈得才、梁成富、赖文光和蓝成春接管了太平军北方残部。这支部队主要由皖北士兵组成,后因内部瓦解而解散。最终,赖文光率部并入捻军,活跃于华北地区的黄淮平原。
【1、枣阳会合】
在淮北亳蒙根据地失陷后,捻军已辗转河南、山东等地将近一年。与此同时,西北太平军本欲回援天京,却在得知天京陷落的消息后军心动摇,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数月间,捻军与西北太平军残部持续在大别山一带迂回游走,屡遭清军围剿而接连受挫。
10月底,霍山县境内战事频仍,捻军与太平军接连激战,部队已显疲态。黑石渡战役中,太平军再度失利,导致扶王陈得才自尽身亡,马融和叛变投敌,仅有赖文光带领数千残部成功突围,向湖北方向撤退。
面对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的紧追不舍,张宗禹、任柱等捻军将领被迫向河南方向撤退。在此生死存亡之际,捻军与太平军残部领袖们深刻认识到,只有摒弃各自为政的现状,进行部队整合,建立统一指挥体系,方能扭转战局,摆脱强敌围剿。
战略战术的革新促成了战局的转变。在枣阳集结期间,部队得以总结经验、制定方案,同时完成了整合与重组。
在枣阳集结后,西北太平军残余力量与捻军合并,形成了被后世称为"后期捻军"的军事力量,这一联合部队也被部分研究者称作"太平天国新军"。
相较于早期阶段,捻军在后期的作战策略实现了显著提升。通过"以骑代步"的转型,骑兵集群成为兵团的核心力量,显著增强了部队的机动性,进而发展出高效的快速机动战术体系。
捻军的作战方式展现出两个显著特征:
部队采取了机动灵活的作战策略,通过高速移动和迂回战术消耗敌方实力,避免过早展开正面交锋。
在发动决定性战役时,需要审慎把握最佳时机和战场位置,强调迅猛果断、快速制胜。战术上可采取伏击围剿,或在清军行军、集结未完成之际发动突袭。当清军连续追击多日导致兵疲马乏时,则可立即调转方向,实施快速反击。
在战术部署上,军队进攻通常运用骑兵四面合围的策略,同时辅以步兵正面推进,形成"数万步兵在骑兵掩护下协同推进"的态势,其攻势迅猛如暴风骤雨,瞬息间便可逼近敌阵。而在防御时,则采取"数十骑兵组成环形阵型,背靠背、马接马"的战术,构成数十甚至上百个这样的防御单元。

清军的包围被他们以分兵突进的方式冲破,同时派遣部分骑兵保护家眷和物资,与敌人周旋,寻找机会成功脱困。
捻军将领们在实战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其军事才能通过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最终凝聚成这套创新的战术体系。
随着太平天国的覆灭,清廷得以调动全国主力部队,全力围剿活动于北方地区的捻军势力。面对清军的强势镇压,捻军被迫采取灵活机动的作战策略,通过快速转移来突破清军的包围圈,以此谋求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
【2、新战法的威力】
在丢失皖北阵地后,捻军未能创建新的根据地,且缺乏生产活动,难以通过稳定渠道获取军需物资,最终被迫依赖掠夺维生。
捻军为摆脱追兵,不得不设法拉开与敌军的距离,以争取时间进行物资补充和休整。
叛军自失守根据地后,为躲避追剿而四处流窜,常依托险要地形休整。经过十余日激战,他们选择突破一侧防线远遁,不惜代价奔袭千里之外。由于当地缺乏防备且无主力部队驻守,匪徒得以大肆劫掠。待我军回师布防时,他们已蚕食殆尽。每当官兵抵达交战,匪徒总能以逸待劳,使我军处于被动应战的劣势。
在占据战略优势位置后,部队进行休整补给,若遭遇敌军且具备交战条件则果断应战,否则立即撤离。
捻军战士以出色的体能著称,他们能够适应恶劣环境并持续行军。无论是骑兵还是步兵,都具备快速移动的能力,前者擅长急行军,后者则以持久奔跑见长。
来自多固、蒙、毫、徐、宿、永、曹、兖地区的百姓,长期从事体力劳动,部分人参与私盐贩卖。这些民众体力充沛,即便沦为盗匪也极具战斗力。他们不仅擅长骑术,更以徒步见长,每日行进百里已是家常便饭。
"常年流动作战磨练出灵活机动的特质"。捻军之所以能快速转移、长途跋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健壮的体格。
得益于创新战术的成功运用,捻军获得了大量战马,士兵们普遍配备两到三匹坐骑,使其在行军途中能够快速换乘,保持高速机动。这种迅捷的移动能力让以步兵为主体、骑兵建设滞后且战马补给匮乏的湘军望尘莫及。
捻军采取"扬长避短"的战术策略,成功开创了有利局面。其"不攻城"的战略选择,一方面源于火药匮乏和攻坚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避免因占据城池而陷入敌军包围,丧失其赖以制胜的机动作战优势。
与枣阳部队汇合后,面对僧格林沁蒙古骑兵的强势压迫,捻军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他们迅速组建骑兵部队,运用新型战术,通过快速撤退摆脱追击,同时伺机寻找战机消灭敌军。
在1864年12月12日和次年1月29日,僧军先后在邓州与鲁山遭遇捻军埋伏,两次战役均以失败告终。通过这两场战役,捻军充分展现了其运动战术的作战效能。

清政府因僧格林沁军队的接连胜利以及捻军、太平军的日渐式微,陷入了一种过度的自信,认定捻军不过是"屡战屡败的乌合之众"。他们深信,凭借僧格林沁的现场指挥,定能将这股势力彻底剿灭。
僧格林沁过于自负,将捻军视为不堪一击的小股流寇,完全忽视了对方兵种和战术的革新。即便接连遭遇两次挫败,他麾下蒙古骑兵的声誉也已一落千丈。
僧氏将战败之责推诿于其他清军"救援不力",同时以"皆不得战"为由拒绝了湘军的支援。他坚信捻军已陷入绝境,遂亲自率领孤军展开追击,企图速战速决,一举歼灭捻军以建立功勋。
【3、高楼寨之战】
面对僧军的围剿,捻军将领们依然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策略,在豫西和鄂北地区迂回周旋,寻找战机。2月中旬,他们抓住两次有利时机,集中兵力反击,成功击退僧军。进入3月末,在河南境内连战连捷的捻军采取南进北撤的迂回战术,从考城挺进山东,继续以快速转移的战术迷惑敌军。
僧格林沁紧随捻军踪迹,常一日之内多次交战,虽屡有斩获,却未能给予致命打击。捻军在短短三十天内,奔袭范围已超过三四千里。
由于山东各地地主武装修建防御工事并实施坚壁清野,切断了捻军的补给线,僧格林沁判断捻军因缺粮而节节败退。基于这一判断,他命令部队持续追击,连续数十日未曾下马休整。
清廷对僧格林沁的孤军冒进深感忧虑,多次发出警告。
各匪首狡诈善战,常以骑兵配合步兵轮番进攻,与以往只知劫掠的捻军大不相同,他们惯用拖延战术消耗清军。僧格林沁虽紧追不舍,却担心兵力过度消耗,因此奉命改道北面进行包抄,强调必须稳扎稳打,避免冒进。
然而,僧军此时已陷入极度疲惫的困境,难以脱身。一方面,由于长期奔波作战,导致士兵伤亡惨重;另一方面,部队中混杂了大量缺乏纪律的外来骑兵。由投降者组成的杂牌军完全无法与僧氏亲自率领的蒙古骑兵协同作战,致使步兵落后,骑兵分散,队伍无法保持统一行动。
僧格林沁性情暴戾,待人苛刻,经常鞭笞甚至处决部下,导致军心涣散。将士们怨声载道,人人自危,纷纷萌生退意,无心恋战。这样的军队,注定难逃败局。

五月初,山东运西水套地区成为了捻军的集结地,他们与郓北的数万潜伏武装力量形成联盟,展现出强大的攻势。凭借显著增强的军力和占据的优越地理位置,捻军领袖们策划在此设下埋伏,准备以静制动,一举消灭敌军。
5月18日,因情报失误,僧格林沁率领部队匆忙赶往荷泽定陶以南,结果白费力气。得知捻军在北面后,他立即调转方向,急行军四十里,导致部队饥疲交加,士气低落,军心涣散。
僧格林沁率部追击至曹州府城西侧的高楼寨时,遭到捻军重重包围。激战持续到深夜,这位将领不幸战死沙场。其麾下部队全军覆没,包括王本军和三省马队在内的精锐力量几乎全部阵亡。
高楼寨之战的告捷,为捻军带来了三重重要价值。
大量清军叛逃士兵加入捻军,使其获得了众多来自关外的精良战马和武器,军事实力显著提升。
尽管捻军起初并非强大势力,但因获得僧格林沁的大量战马,实力大增。如今这支队伍已成长为不容小觑的劲敌。
左宗棠曾坦言,这股捻军的凶悍源于僧格林沁和多隆阿败军被其裹挟,因担心无法获得宽恕而背信弃义,调转枪口。其中以来自黑龙江的三盟士兵最为突出,他们精通骑射、骁勇善战,确实令湘淮军难以招架。
通过歼灭僧格林沁这支清廷精锐骑兵,捻军不仅消除了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更彻底打乱了清政府的战略部署——原本计划由僧军从北方南下,与曾国藩的湘淮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这一关键胜利使战局发生根本性转变,捻军成功掌握了战争主导权。
捻军在枣阳会师后实施的机动灵活、以快制胜的战略战术被证实成效显著。这种作战方式已被捻军将士熟练掌握,并逐步发展为该部队的核心战术体系。
【4、高楼寨大捷的意义】
在枣阳集结后,捻军的组织架构和特征发生了显著转变。
捻军经历了显著的转型,从以往"亦民亦兵"的松散组织转变为专业化的军事力量。由于清军完全掌控了皖北地区,他们失去了稳固的战略依托。在这种情况下,这支军队并未选择开辟新的据点,而是采取了持续移动的作战策略,将不停转移作为主要的生存手段。
在组织架构方面,捻军与太平军这两支同盟部队摒弃了以往各自为政的状态。他们保留了捻军原有的编制体系,同时借鉴了太平军的特色管理模式,运用其"军法诡谋"来整饬部队。

后期捻军在作战指挥方面实现了高度统一,展现出显著的战术素养。其部队行动迅捷,指挥体系灵活机动,将士作战勇猛且纪律严明,进退有度,已然形成一个完整的战斗体系。这种转变充分体现了捻军正规化水平的显著提升,正如时人所评:"已非昔日流寇式的劫掠武装所能比拟。"
捻军运动在后期阶段延续了早期的特点,虽然保持着强烈的反清立场,却始终未能确立明确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目标。
赖文光在其《自述》中透露了枣阳会晤期间"期望早日复国"的想法,这仅仅反映了太平军残部试图借助捻军力量重振太平天国的个人意愿。然而,这一计划并未获得捻军领导层的认可与协助。
清朝官员普遍认为,尽管捻军后期势力庞大难以剿除,但其威胁有限,既"无法动摇国家根基",也"难以构成实质危害"。
通过对比研究,学者们将后期捻军与太平军进行了深入分析,最终得出了以下结论:
流寇既无根据地,又缺乏物资储备,既无战略部署,也无明确旗号,不过是一群无谋略、无归宿的乌合之众,相较于正规叛军,实属不堪一击。
事实充分证实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后期捻军延续了早期特征,未能制定明确的政治斗争纲领和长远战略规划。在"无大志"思想主导下,他们采取游击战术与清军周旋,仅在遭遇清军追击时才被动应战,通过打击追兵维持生存。由于始终未能掌握战略主动权,最终导致了其覆灭。
【5、捻军的失策】
在高楼寨一役中,捻军成功击溃了对其构成严重威胁的清军主力。此战后,清廷在北方地区已无任何军事力量能够与捻军抗衡。与此同时,湘淮军主力仍滞留于长江沿岸,而捻军凭借其强大的骑兵部队,完全掌控了长江以北广大区域的战略主导权。
捻军统帅们抓住湘淮军未至、清廷防务薄弱的战略机遇,能够立即谋划直击敌军关键、持续消灭敌方力量、巩固战果并建立华北根据地的宏图大计。
由于京畿和直隶地区清军防守力量严重不足,黄河成为唯一的北方防线。清廷最为担忧的是捻军突破黄河防线北上。继僧格林沁之后负责剿捻的曾国藩对此深感忧虑,他认为:"若叛军不渡黄河,剿灭尚不算太难;一旦渡河,必将引发混乱,众目睽睽之下,难免遭人非议,我实在难以应对,恐怕难以避免重大过失。"
清廷紧急派遣兵部左侍郎崇厚率领洋枪队前往济河布防。同时,曾国藩迅速命令潘鼎新带领十营淮军经海路驰援天津,并调派刘铭传火速支援山东,以阻止捻军北渡黄河。

然而,捻军领导层在确定行军路线时举棋不定,难以做出明确决策。
王僧氏部队战败后,军心大乱。抓获的密探透露,叛军首领牛洛红与张宗禹、赖文光、陈大喜等人正就下一步行动展开激烈讨论:有人主张攻打济南,有人提议北上直隶,还有人建议渡过黄河从河南进军陕西,各方意见难以统一。
捻军的战略决策陷入僵局,导致其军事行动缺乏统一规划。他们先后在曹县、单县一带构筑防御工事,强占民寨,修建堡垒以抵御清军;随后又转移至黄河南岸,通过水路对河套地区展开袭扰;同时,濮州地区也遭到其侵扰,当地船只被征用,树木被砍伐用于制造船筏,显示出北上意图。这支起义军长期在鲁西南的黄河以北、运河以西区域游移不定。
6月底,竞分股分批撤离,最终抵达皖北大本营。
皖北地区的战略价值已被捻军视为重建势力版图的关键,他们计划重新夺回蒙城、亳州等传统据点并壮大军事力量。然而,这一区域的环境与局势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不再具备支撑捻军发展的基础条件。
1863年,清军重新掌控该区域后,立即展开大规模整顿。圩寨被彻底拆除,民间武器被全面收缴,通过强化管理措施,当地秩序得以重建。
由于临近湘淮军及皖豫地方军的驻扎区域,清军得以快速集结,对捻军形成合围之势。在持续月余的雉河集战役中,尽管捻军攻占了周边多个村镇和圩寨,却始终未能攻陷涡阳县城。面对清军的多路夹击,捻军不得不放弃收复蒙亳的计划,转而采取游击战术。
针对捻军领袖重建根据地的计划与举措,虽不能全盘否定其合理性,但从当时清军与捻军的战局分析,更为明智的战略选择应是把握战机,立即北渡黄河,避开清军主力部队,在华北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
然而,捻军内部意见分歧,决策迟缓,对北上黄河的计划仅作试探性尝试后,便贸然转向,与清军主力正面交锋,选择向南推进。
捻军领袖们在"流寇主义"影响下,已完全失去战局掌控力,这充分暴露了他们无法制定合理战略规划的致命缺陷。
这场战争的战略主导权始终未能被他们所掌控。
高楼寨之战后,捻军领导层在行军路线上出现严重分歧,决策过程陷入僵局,这一现象充分反映了其战略指挥体系存在重大漏洞。
【6、捻军有没有最高统帅?】
捻军尚未形成统一的指挥体系和领导核心,最高统帅职位依然空缺。各部队行动缺乏协调,处于各自为政的分散状态。
捻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展现出显著的组织特性,其突出表现为强烈的排外倾向与频繁的内部分化。
捻军作为一支地方农民武装,其组织基础建立在血缘与地缘关系之上,这种宗族同乡的紧密联结深刻塑造了其本质特征。这种联结方式在单股或单旗内部发挥着强大的凝聚效应,然而在不同旗股之间却形成了显著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不仅阻碍了各旗之间的协作与联合,还频繁引发内部冲突与对立。
在1855年,尽管张乐行以"大汉盟主"的身份整合了捻军各旗,但这一统一仅是形式上的。实际上,各旗依然保持着自主权,且彼此间的对立与冲突始终持续不断。
自1864年起,捻军在北方反清运动中陷入孤立境地。面对生存压力,各旗势力采取联合策略,形成统一阵线以应对清军威胁。

由于捻军被迫撤离皖北根据地,在流动作战过程中吸纳了大量太平军残部、清军散兵以及各地失地农民,其成员构成日益多元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有的血缘和地域特征。
捻军领导层及其核心成员依旧延续了传统特征。在枣阳会师中,其组织结构未作调整,继续沿用基于家族与地域的五色旗制度。各旗控制权仍掌握在原有领袖及核心人员手中,人员轮换也严格遵循血缘关系体系。
牛洛红牺牲后,其子牛遂接管部队,任柱阵亡则由其弟任宗三继任,张宗禹的部队则一直由其家族成员严密掌控。李鸿章因此评价后期捻军"家族世代相随,父兄亡故子弟继任,宛如遵循家族传统"。
捻军后期仍保持着原有的血缘和地缘特征,这种状况决定了各旗之间难以实现紧密联合。各旗之间既存在相对独立性,又潜藏着内部矛盾,这使他们的联盟注定松散且难以持久。相反,旗际间的纷争与分裂成为常态,无法避免。
作为太平军残余势力的领袖,赖文光虽与捻军无亲缘或地域联系,且仅掌握数千兵力,其被推举为联军最高指挥官的事实引发了诸多疑问。这种缺乏传统纽带与军事实力支撑的领导地位,使捻军各部首领的拥戴行为显得颇为耐人寻味。
据民间流传的说法,东捻军的实际领导者并非赖文光,而是任化邦。这支主要由蒙城和亳州人组成的起义军,绝大多数成员都选择听从任化邦的指挥。这一说法对赖文光作为后期捻军或东捻军首领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
赖文光麾下仅掌控数千太平军,均为南方籍将士,却始终难以融入当地。任化邦阵亡后,其部队主力尚存,待众人安葬鲁王后,因失去奋斗方向而自行解散。"赖文光并非捻军最高统帅,真正的领袖当属张宗禹与任化邦。"

历史资料确凿显示,捻军后期并未设立所谓的"最高统帅"一职。因此,赖文光自然无法担任这个根本不存在的职务。
由于后期捻军内部缺乏强有力的统一指挥体系,各支力量之间互不统属,加上其不断经历分裂与重组,直至最终瓦解,这一系列史实充分表明,这支农民武装始终未能形成严密的组织架构和集中统一的军事体系。
捻军后期领导层未能形成清晰的政治纲领,也未提出政权诉求,这使得他们无法制定相应的战略部署,更难以统一指挥各支部队的作战方向。
杠杆炒股官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